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,权威,专业,及时,全面,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!
芦哲 占烁 李昌萌(芦哲系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)
核心观点
我们利用43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的消费数据,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对我国消费结构进行国际比较。数据年份如无特别说明均为2019年,关于样本国家和数据的详细说明参考正文第四节附录部分。主要结论如下:
1、我国消费率偏低是服务消费影响吗?我国整体消费率偏低,服务和商品消费都有待提高,并不是商品消费高、服务消费低。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.3%=服务消费率21.1%+商品消费率18.2% ,而43个国家居民消费率为55.2%=服务消费率28.4%+商品消费率26.8%。我国商品消费率比43国平均水平低8.6个点,服务消费率比43国平均水平低7.3个点,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。
我国服务消费比重真的低吗?不低。跟人均GDP在2.5万美元以上的国家相比,我国服务消费比重是偏低的;但跟人均GDP在2.5万美元以下的国家相比,我国服务消费比重不低。把43个国家服务消费比重跟人均GDP结合来看,43个国家里,有20个国家2019年人均GDP在2.5万美元以下,这些国家服务消费比重平均为46.4%;有23个国家人均GDP在2.5万美元以上,这些国家服务消费比重平均为56.3%。我国2019年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、服务消费比重53.8%,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大部分国家。
2、接下来,我们对服务消费做一个结构比较,主要结论:
(1)我国消费偏好更注重基础服务消费,呈现出“重教育不重娱乐、重买房不重租房”的特点,住房、医疗、教育等基础服务是我国服务消费比重较高的主要原因。
(2)我国服务消费价格偏低,典型如交通费用。服务价格低的好处是避免了“鲍莫尔病”,教育、医疗、交通等大量基础服务消费,对于低收入者也能负担;坏处是制约了服务消费比重的提高,服务消费额的比重受到价格限制,消费量的比重可能更高。
3、对于具体的服务消费类别,国际比较结果如下:
(1)按照消费支出的八大类来看,我国与其他国家消费结构差别不大。八大类消费支出里,我国的结构大多跟国际水平比较一致,这说明各国消费者,无论面临怎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环境,消费需求大致是相似的。差别最大的是“其他用品与服务”。我国为2.4%,43国平均为10.6%。但这更多来自于统计差别,一是个人护理的支出,二是金融服务消费支出的差别。
(2)居住:我国折算租金和住房维修支出比重高、实际租金占比低。一是自有住房折算租金,2019年我国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占消费比重为15.1%,43国平均为12.5%,其中美国12%、欧盟12.4%、日本16.2%。
二是住房维修服务,我国比重为3.2%,43国平均为0.7%,其中欧盟27国为1.0%,美国日本缺少该项数据。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毛坯房交付比例较高,硬装支出远高于国际水平,抬高了整体装修支出。
第三,尽管自有住房折算租金比重高于国际水平,但是我国实际房租占消费比重仅为1.1%,远低于国际平均3.7%。这是因为我国租房市场规模低于国际水平,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租房家庭占比只有21.1%,而美国、日本都在三分之一左右。从时间趋势来看,我国实际房租支出受到城镇人口数量影响较大,2023年后,随着新增城镇人口数量的回升,房租支出占比也在回升。
(3)教育:家庭教育支出比重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。我国教育支出有4个特点:第一,家庭投入远高于其他国家。教育支出占消费比重是8.4%,43国平均仅为1.4%,我国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超过其他支出,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。
第二,我国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小,属于必选消费。中国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.3,基本属于不受收入变动影响的必需品,东亚国家里韩国的教育弹性也较小,仅为0.54,日本较高达到1.72,另外美国1.76、巴西3.9,这些国家教育的支出弹性更大,更接近奢侈品。
第三,我国教育支出比重跟家庭收入成反比,收入越低的家庭,教育支出比重越高。根据北京大学《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(2021)》的数据,收入最靠后的10%家庭里,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达到21.2%,收入最靠前的10%家庭这一比重为8.4%。
第四,中国家庭的教育支出主要花费在校内,而非校外培训;不同学段来看,小学阶段校外培训花费较多。从幼儿园到高中、中职,不同学段的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支出比重的平均值只有12.9%,最高的是小学阶段,占比26.2%。
(4)医疗:我国医疗服务支出占比6.4%,43国平均是2.7%。跟43个样本国家比较,我国排在第二位,最高的是美国,医疗服务支出占消费比重达到17.6%。美国医疗支出比重较高的原因是医疗服务价格昂贵,我国则是由于医保和商业保险都起步较晚。从世卫组织(WHO)统计的各国医疗总支出和私人支出两个指标来看,我国医疗总支出并不高,占居民消费的13.7%,低于43国平均16.2%的水平;但我国私人医疗支出占到消费的6.0%,高于43国4.6%的水平。
(5)交通通信:邮递服务占消费比重高、其他服务占比低。2019年我国邮递服务消费比重较高,为0.3%,43国平均为0.1%,这与我国发达的电商网络和快递系统有关,但邮递服务在居民消费中的整体比例普遍较小。通信服务支出比重差距不大,中国为1.8%,43国平均为2.1%。
交通服务差距较大,我国支出比重明显低于其他国家。一是交通费,我国为1.7%,43国平均为2.6%,这与我国较低的交通价格有关,公交、地铁、铁路等出行费用都不高。按照Numbeo统计的本地出行单程票价来看,中国是0.42美元,43国平均是2.19美元。二是交通工具使用和维修,我国为1.1%,43国平均为6.7%。这可能与汽车保有量有关,我国每千人汽车保有量为231辆,43国平均为600辆,更多的汽车保有量也意味着更多的保养维修支出。
(6)文娱消费:我国文娱消费比重大幅低于其他国家,不仅是服务消费占比,商品消费比重也明显偏低。文娱商品消费包括文娱用耐用消费品、其他文娱用品两类,我国文娱耐用品消费占比0.7%,低于43国平均1.7%;其他文娱用品0.8%,低于43国平均2.6%。服务消费方面,我国文娱服务比重仅为0.6%,低于43国平均3.4%。
但是我国旅游消费占比并不低,2019年我国旅游消费比重为1.2%,43国平均为1.1%。
(7)餐饮住宿:我国餐饮服务消费占比不低,但住宿服务比重偏低。2019年我国餐饮服务占消费比重为6.4%,43国平均为6.6%,大致相当。但我国住宿服务比重明显偏低,在居民消费分类里,住宿服务计入“其他服务”项,而2019年其他服务比重只有1.2%,住宿服务预计低于1%,相比之下43国住宿服务占消费比重达到2.0%。
风险提示:(1)国际比较在细节上可能存在误差,各国统计制度的差异未能完全反映,如在个人护理、餐饮住宿、金融服务等服务项目统计上差别较大,这不影响我们的整体结论,但可能带来一定的统计差异风险。(2)数据相对滞后,由于2020-2022年各国受疫情影响较大,服务消费数据偏差大,2023年后数据大多还没有更新,2019年数据较为齐全和稳定,但时间距离较远,可能产生一定偏差风险。(3)国际比较的广度仍有不足,如目前的数据大多是欧洲国家,对亚洲国家的样本覆盖面仍有不足,不能完全排除国际比较带来的结论片面性。
内容目录
1. 总量:我国服务消费水平真的低吗?
2. 结构:服务消费的领先与落后
2.1. 八大类消费支出结构差别不大
2.3. 居住:我国折算租金高、实际租金低
2.4. 教育医疗: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.
2.5. 交通通信:邮递服务高、其他服务低
2.6. 文娱和餐饮住宿
3. 总结:中国服务消费的三个特点
4. 附录:数据说明
5. 风险提示
正文
我们在此前报告中按照自上而下的逻辑,基于38个国家的比较数据,对中国消费率进行了拆解和国际比较。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我国居民消费率低的原因主要是消费倾向低,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并不低(《基于38个国家的比较:为何我国消费率偏低》)。
接下来,我们将按照自下而上的逻辑,从消费的构成来拆解支出结构,研究我国服务消费是否偏低,如果是,哪些领域偏低。本文所选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为2019年数据,关于样本国家和数据的详细说明参考第四节附录部分。
1. 总量:我国服务消费水平真的低吗?
总量比较方面,我们选择了有可比数据的43个国家进行居民消费的拆解比较,包括欧洲30个、亚洲5个、北美3个、南美洲3个、非洲大洋洲各1个,除了印度、韩国、中国,其余均来自OECD数据库。
当我们做国际比较时,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我国的服务消费统计还不完善。今年3月,中办国办印发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指出:“健全服务消费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统计监测,加强买方分地区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统计,完善全口径消费统计制度”。
我国目前服务消费数据有三个口径。第一个口径是2018-2022年统计局曾经公布货物和服务消费比重,2019年服务消费占比53.8%。第二个口径是城乡居民一体化调查里的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,2019年服务消费占比是45.9%。第三个口径是2023年7月开始公布的服务零售额,从销售者而非消费者的角度统计服务消费,但目前这个指标仅公布累计增速,2025年前5个月累计增速5.2%。
哪个指标更能反映服务消费的真实情况?我们认为2019年服务消费比重53.8%可能较为合理。这是因为,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的统计里缺少两大类,一是金融中介服务,二是保险服务。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在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使用核算研究》一文中指出,“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支出比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多出两个类别,一是金融中介服务,二是保险服务”。而我们用43个国家的消费数据发现,在有数据的35个国家里,金融和保险服务占消费的比例大致是5%左右。因此,宏观的居民服务消费应该明显高于微观调查的45.9%。
由此,我们得到第一个结论:我国消费率偏低,服务和商品消费都有待提高,并不是商品消费高、服务消费低。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.3%=服务消费率21.1%+商品消费率18.2%,而43个国家居民消费率为55.2%=服务消费率28.4%+商品消费率26.8%。我国商品消费率比43国平均水平低8.6个点,服务消费率比43国平均水平低7.3个点,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。


从消费结构来看,我国服务消费比重真的低吗?不低。跟人均GDP在2.5万美元以上的国家相比,我国服务消费比重是偏低的;但跟人均GDP在2.5万美元以下的国家相比,我国服务消费比重不低。把43个国家服务消费比重跟人均GDP结合来看,43个国家里,有20个国家2019年人均GDP在2.5万美元以下,这些国家服务消费比重平均为46.4%;有23个国家人均GDP在2.5万美元以上,这些国家服务消费比重平均为56.3%。我国2019年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、服务消费比重53.8%,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大部分国家。


2. 结构:服务消费的领先与落后
进一步,我们将中国的服务消费结构与43个国家的服务消费结构进行比较,看看我国的服务消费项目哪些强、哪些弱。
2.1. 八大类消费支出结构差别不大
按照消费支出的八大类来看,我国与其他国家消费结构差别不大。八大类消费支出里,我国的结构大多跟国际水平比较一致,这说明各国消费者,无论面临怎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环境,消费需求大致是相似的。
差别最大的是“其他用品与服务”。我国为2.4%,43国平均为10.6%。但这更多来自于统计差别,一是个人护理的支出,国际口径放在“其他用品与服务”项目下,我国放在“生活用品及服务”项目,2019年个人护理占我国消费支出的1.2%。
二是金融服务消费支出的差别。43国金融中介和保险服务占消费比重合计约5%,计入“其他用品与服务”项目,而我国居民消费调查里没有金融相关支出。


2.2. 居住:我国折算租金高、实际租金低
我国居住服务里大多项目占比都高于国际平均水平。一是自有住房折算租金,2019年我国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占消费比重为15.1%,43国平均为12.5%,其中美国12%、欧盟12.4%、日本16.2%。
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占消费比重一般受房价收入比影响较大。住房作为一种市场化资产,据此产生的住房服务应在生产范围内,作为自给性生产活动,由房主消费,计入GDP。不同国家对自有住房服务计入GDP的核算方式不同,有市场租金法和建造成本法两种。国际惯例是,租房市场发达国家用市场租金作为自有住房的虚拟价值,而租房市场不发达国家用建造成本作为虚拟价值。我国自有住房消费实际上存在宏观和微观两种核算方式,宏观是按照成本法核算城镇自有住房消费,直到“五经普”才改为市场租金法,微观住户调查是按照市场租金法核算自有住房消费。
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行,近几年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的比重有所下降,2023年降至14.1%。

二是住房维修服务,我国比重为3.2%,43国平均为0.7%,其中欧盟27国为1.0%,美国日本缺少该项数据。我国住房维修服务消费比重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,主要原因可能是毛坯房交付比例高,硬装支出远高于国际水平,抬高了整体装修支出。根据奥维云网发布的《2024年中国房地产精装修市场蓝皮书》,过去几年我国精装项目渗透率长期在30-40%之间,低于国际水平。
尽管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占比高于国际水平,但是我国租赁房房租占消费比重仅为1.1%,远低于国际平均3.7%。这是因为我国租房市场规模远低于国际水平,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租房家庭占比只有21.1%,而美国、日本都在三分之一左右。从时间趋势来看,我国实际房租支出受到城镇人口数量影响较大,2023年后,随着新增城镇人口数量的回升,房租支出占比也在回升。


2.4. 教育医疗: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
我国教育支出和医疗服务支出比重都远高于国际水平。
我国教育支出有4个特点:第一,家庭投入远高于其他国家。教育支出占消费比重是8.4%,43国平均仅为1.4%,我国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超过其他支出,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。
第二,我国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小,属于必选消费。中国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.3,基本属于不受收入变动影响的必需品,东亚国家里韩国的教育弹性也较小,仅为0.54,日本较高达到1.72,另外美国1.76、巴西3.9,这些国家教育的支出弹性更大,更接近奢侈品。
第三,我国教育支出比重跟家庭收入成反比,收入越低的家庭,教育支出比重越高。根据北京大学《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(2021)》的数据,收入最靠后的10%家庭里,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达到21.2%,收入最靠前的10%家庭这一比重为8.4%。
第四,中国家庭的教育支出主要花费在校内,而非校外培训;不同学段来看,小学阶段校外培训花费较多。从幼儿园到高中、中职,不同学段的校外培训支出占教育支出比重的平均值只有12.9%,最高的是小学阶段,占比26.2%。




我国医疗服务支出占比6.4%,43国平均是2.7%。跟43个样本国家比较,我国排在第二位,最高的是美国,医疗服务支出占消费比重达到17.6%。美国医疗支出比重较高的原因是医疗服务价格昂贵,我国则是由于医保和商业保险都起步较晚。从世卫组织(WHO)统计的各国医疗总支出和私人支出两个指标来看,我国医疗总支出并不高,占居民消费的13.7%,低于43国平均16.2%的水平;但我国私人医疗支出占到消费的6.0%,高于43国4.6%的水平。医疗总支出低、私人支出高,背后的原因是我国医保体系和商业医疗保险都起步相对较晚,距离国际水平还有一定差距。


2.5. 交通通信:邮递服务高、其他服务低
交通通信下面有4个服务科目,我国合计是4.9%,43国平均是11.5%。
具体来看,我国邮递服务消费比重较高,为0.3%,43国平均为0.1%,这与我国发达的电商网络和快递系统有关,但邮递服务在居民消费中的整体比例普遍较小。
通信服务支出比重差距不大,中国为1.8%,43国平均为2.1%。
交通服务差距较大,我国支出比重明显低于其他国家。一是交通费,即各种公共交通、铁路、航空的消费,我国为1.7%,43国平均为2.6%,这与我国较低的交通价格有关,公交、地铁、铁路等出行费用都不高。按照Numbeo统计的本地出行单程票价来看,中国是0.42美元,43国平均是2.19美元。
二是交通工具使用和维修,我国为1.1%,43国平均为6.7%。这可能与汽车保有量有关,我国每千人汽车保有量为231辆,43国平均为600辆,更多的汽车保有量也意味着更多的保养维修支出。



2.6. 文娱和餐饮住宿
我国文娱消费占比大幅低于其他国家,不仅是服务消费,商品消费占比也明显偏低。文娱商品消费包括文娱用耐用消费品、其他文娱用品两类,我国文娱耐用品消费占比0.7%,低于43国平均1.7%;其他文娱用品0.8%,低于43国平均2.6%。服务消费方面,我国文娱服务比重仅为0.6%,低于43国平均3.4%。
但是我国旅游消费占比并不低,2019年我国旅游消费比重为1.2%,43国平均为1.1%。
最后是餐饮住宿,我国餐饮服务占比不低,但住宿服务占比偏低。2019年我国餐饮服务占消费比重为6.4%,43国平均为6.6%,大致相当。但我国住宿服务比重明显偏低,在居民消费分类里,住宿服务计入“其他服务”项,而2019年其他服务比重只有1.2%,住宿服务预计低于1%,相比之下43国住宿服务占消费比重达到2.0%。

3. 总结:中国服务消费的三个特点
综合上述国际比较来看,中国服务消费有三个特点:
一是服务消费在消费结构里的比重不低。我国2019年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、服务消费比重53.8%,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大部分国家。
二是消费偏好更注重基础服务消费,呈现出“重教育不重娱乐、重买房不重租房”的特点,住房、医疗、教育等基础服务是我国服务消费比重较高的主要原因。
三是服务消费价格偏低,典型如交通费用。服务价格低的好处是避免了“鲍莫尔病”,教育、医疗、交通等大量基础服务消费,对于低收入者也能负担;坏处是制约了服务消费比重的提高,服务消费额的比重受到价格限制,消费量的比重可能更高。

4. 附录:数据说明
中国的消费结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《住户调查统计年鉴》,交通、教育文娱两个类别涉及细分项目数据,是利用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测算权重得到,测算所用的样本数据时间是2016-2023年。
国际比较的数据来自于OECD,总量和结构数据样本有所不同。总量数据是指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两个大类占比,除了印度、韩国来自于CEIC,其余均来自OECD数据库。结构比较是后面的具体类别消费支出比较,都来自于OECD数据库。总量比较的43个样本国家包括欧洲30个、亚洲5个、北美3个、中南美洲3个、非洲大洋洲各1个。结构比较的43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30个、亚洲3个、北美3个、中南美洲3个、大洋洲2个、集合地区2个(欧元区和欧盟)。在具体结构比较时,并非43个国家和地区数据都是完整的,部分品类存在数据不全的问题,如43个国家和地区里只有37个国家有实际房租数据,这些我们都取简单平均。
由于涉及消费结构比较,我们这里选择2019年数据,这是因为2020年-2022年各国服务消费普遍受到疫情影响,消费结构不具有代表性,而2023年后的数据样本较少,2019年数据相对稳定且全面。
5. 风险提示
(1)国际比较在细节上可能存在误差,比如各国统计制度的差异未能完全反映,如在个人护理、餐饮住宿、金融服务等服务项目统计上差别较大,这不影响我们的结论,但可能带来一定的统计差异风险。
(2)数据相对滞后,由于2020-2022年各国受疫情影响较大,服务消费数据偏差大,2023年后数据大多还没有更新,2019年数据较为齐全和稳定,但终究距离较远,可能产生一定偏差风险。
(3)国际比较的广度仍有不足,如目前的数据大多是欧洲国家,对亚洲国家的样本覆盖面仍有不足,不能完全排除国际比较带来的结论片面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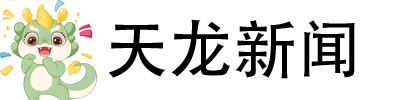
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





